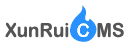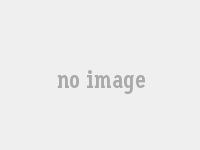白玉镂雕香囊。北京大学出版社供图
明清时期,由苏式、苏工、苏服、苏器、苏食等组成的“苏作”,代表了当时全国最高的工艺水准和最流行的消费时尚。如张瀚《松窗梦语》说:“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贵吴器,而吴益工于器。”它们不仅为市井百姓所追捧,也成为帝王之家的首选。
《故宫里的江南——清代宫廷珍玩与苏作》一书,集中呈现了古代苏州制造与紫禁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其中,苏州向紫禁城输送的大批杰出的玉匠,还有他们设计制作、精美绝伦的玉器,是这部“双城记”中最富魅力的篇章。
远承良渚,温润有方
说到清代的苏州,很多人会首先想到徐扬的《姑苏繁华图》,织造、雕刻、制陶等手工业作坊,是这幅画的重要表现内容。其中一定有不少制作玉器的匠人和铺子,这与苏州作为当时玉器制造中心的地位密切相关。
苏州玉作,历史悠久,传承有序,工艺精良,这主要有3方面的原因。
从文明基因和传承上,苏州玉作远承5000年前的良渚文明。良渚时代的玉器制作,已涵盖切割、打磨、雕刻等工艺,工匠们还掌握了阴刻、浅浮雕等技法。明清时代的苏州玉器制作,借鉴了良渚时期的工艺、形制、纹饰等,并有自己的技法创新。
在文化和精神性格上,苏州在玉作方面的独特禀赋和才能,得益于江南地区稻作文明的涵养。与北方靠天吃饭的旱作农业不同,稻作农业的生产环节更加复杂、细碎,在选种、育苗、插秧、灌溉、施肥、除草、收割等方面都需要精耕细作,久之培养出注重细节、耐得琐碎和持之以恒的文化性格,从业者特别适合从事刺绣、玉雕、木雕等手工艺生产。
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的角度看,玉作的形成与苏州的繁荣密不可分。玉在中华文化中十分特殊,具有权力、财富、人格、生活品味、审美情趣等象征意义。同时,无论是良玉的开采,还是美器的加工制作,都需要强大的经济基础作支撑。明清时期的苏州,是江南乃至全国的经济、商业、文化中心,也是文人雅士、手工业者、商人的聚集地,从工艺技术、美学标准、市场销售等方面,为“苏作”的形成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全要素的保障。
以大运河为纽带,从民间走向宫廷
如同瓷器、木雕等,玉器也有“民间”和“宫廷”之分。苏州玉作很早就形成了自成一体的风格特色,但直到进入紫禁城前,还处在“杨家有女初长成”的阶段。
明清以来,以京杭大运河为纽带,以头脑灵活、手艺精湛的玉匠和他们设计、制作的精美玉器为中介,在相隔千里的苏州和北京之间,终于搭建起一条“水上玉器之路”,实现了苏州玉作从“民间”向“宫廷”的飞跃。
此后,借助帝王也可以说是整个国家的财力智力支持,从选料、设计到制作,苏州工匠彻底摆脱了物质条件的约束,可以不计成本、以最高标准来实现艺术家的梦想。举一个例子,苏州人、宫廷设计师姚宗仁,在乾隆六年(1741年)设计了青玉凫纸样,但直到6年后,才在苏州雕琢而成,这是普通工匠想都不敢想的。

乾隆御题白玉赤壁图山子。北京大学出版社供图
在苏州玉器发展史上,明代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一般说来,明代玉器注重实用性,总体特点是“稚拙有余而精细不足”,因此也被戏称为“粗大明”。明代苏州的玉作,最初也深受其影响。但随着工匠改进了镂雕、浮雕等技法,一种以简洁、典雅、线条流畅、造型和谐为主调,带有鲜明江南文化和美学精神的苏作特色和风格逐渐形成,日益完善。如故宫藏的青玉镂雕枝叶葵花杯、“子刚”款青玉合卺杯等,就完美体现了苏州工匠在镂雕技法上的创新;故宫藏的青玉乳丁纹圭,则是浮雕技法创新的代表。
明代苏州玉作的代表人物,自然是有“玉雕圣手”之称的陆子冈。他是当时苏州府下辖的太仓州人,自幼在苏州学艺,后开办玉器作坊,创造了闻名于世的“子冈牌”。他的玉雕以刀法细腻、构思巧妙著称,同时还将印章、书法、绘画等元素融入作品之中,形成了以“空飘细”为特点的独特艺术风格。他也被后世弟子奉为琢玉业的祖师爷。
到了清代,苏州玉作进入黄金时代,既有宫廷艺术的华丽繁复,又有文人艺术的清雅含蓄,包容了中华美学“错彩镂金”和“出水芙蓉”的两大理想追求。如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白玉仿古铜纹出戟方觚,玉质温润,设计巧妙,技法精湛,形制端庄,纹饰精美,特别是在雕刻兽面纹和云雷纹时,体现了苏州玉匠“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审美追求和高超技艺,成为明清仿古玉器的杰出代表。
乾隆一朝,苏州玉匠为宫廷制作了玉山子、玉壶、玉瓶等玉器,其中不少都进贡给了皇帝本人。它们既满足了皇家的审美与日常生活需求,也推动苏州玉作走上了工艺技术和美学的巅峰。

《故宫里的江南》。北京大学出版社供图
出身于苏州专诸巷玉工世家的姚宗仁,雍正七年(1729年)由年希尧选送至清宫造办处,从事皇家用玉的设计与制作,时间长达24年,对清代宫廷玉器的设计风格、工艺技术、审美标准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继承了祖、父两代的琢玉技艺,能熟练运用各种雕刻技法。由他本人设计、制作的洪字七号璧、荒字八号白玉斧佩等,可以说代表了清代宫廷制玉的最高水准。
又如由苏州织造选送入京的朱彩,是乾隆朝宫廷造办处的刻字玉工。他工艺高超,特别是悟性很高,在刻字时能准确呈现皇帝的旨意,备受赏识。收录于《乾隆宝薮》的“乾隆宸翰”和“惟精惟一”玉玺,是朱彩刻字技艺的杰出代表。他还创造了两个“第一”:一是在为青玉《御制九符》册刻诗时,乾隆特许他在末页刻下“小臣朱彩奉敕恭镌”的款识,这是目前在清代宫廷玉器中唯一留有匠人姓名的玉作;二是据清代皇宫玉器制作活计记录,他也是在该档案材料中名字出现最多的苏州玉工。
帝王与工匠的相互需要,将玉器制作推向高峰
表面上花团锦簇、锦衣玉食的宫廷,内里却是机关重重、步步惊心。在这种极端紧张、压抑、焦虑,乃至朝不保夕的环境和生活中,玉石的温润柔和,玉器象征的纯洁、坚贞、和平、吉祥等,是治愈人们内心焦虑创伤、暂时忘却现实矛盾与纷争的一剂良药。
数百年来,在紫禁城和苏州,在帝王和苏州工匠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需要的良性循环。一方面,处在政治斗争漩涡中心的帝王,需要从精美的苏州玉器中获得心理补偿和审美慰藉,因此不计成本地为后者施展才华提供支持;另一方面,苏州工匠则借助最高统治者提供的物质生活优渥、文化条件完善的舞台,创造出巧夺天工的各种精美玉器,成为照进紫禁城的光亮,同时把中国玉器制作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在形式方面,苏州玉匠的镂雕、浮雕、阴刻等技法,如陆子冈对玉牌边缘的处理、面上纹饰的雕刻,如姚宗仁在设计制作中对线条臻于炉火纯青的处理和运用,如朱彩的兼刻繁复细密的锦地纹、雷纹等,均作为玉雕工艺的典范,并被后世工匠奉为圭臬。
在艺术风格方面,明清时期的苏州玉作是中国玉文化、玉器艺术的瑰宝,特别是带有江南特色、简洁典雅的玉作美学,突出了玉器的自然之美和工艺之精,极大影响了后世玉器的制作和鉴赏。
最后要说的是,这里讲的苏州玉作,只是苏州与紫禁城联系的纽带之一。在本书中,还讲到其他很多方面,如帝王南巡的足迹、北京城仿建江南景物与园林等,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历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开卷有益的。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中国大运河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刘士林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