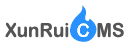电影的幕后故事
Se7en
解谜《七宗罪》
——大卫·芬奇电影解谜
●
○
○

◂(1995)▸
导演: 大卫·芬奇
编剧: 安德鲁·凯文·沃克
主演: 摩根·弗里曼 / 布拉德·皮特 等
类型: 剧情 / 悬疑 / 惊悚 / 犯罪
制片国家/地区: 美国
语言: 英语
上映日期: 1995-09-22(美国)
片长: 127分钟

“想要让别人听你的,光拍拍肩膀是不够的,你必须给他们致命一击,”约翰·多伊(凯文·史派西饰)对萨默赛特警官( 摩根·弗里曼 饰 )和米尔斯警官(布拉德·皮特饰)说道,“这样他们才会听你的”。
用锤头“致命一击”的电影作品,容易使人联想到粗糙拙劣的东西,或是基于巧合呈现的表现主义。萨默赛特警官在《七宗罪》开头,一起普通的谋杀案现场,看到了类似杰克逊·波洛克的“滴色画”。他叹了口气说:“看看那墙面,就知道有多冲动了。”不过随后,整部电影的剧情通过一系列细腻的镜头展开,节奏就像萨默赛特书房里的节拍器那样精准。
电影的几处爆点也经过精心布置,像博物馆展览一样给观众以视觉冲击力。在画廊的比喻中,艺术家将出格的行为作为沟通媒介,并向观众进行说教。约翰·多伊独具创新的“击打”有现实原型。1971年,美国艺术家克里斯·伯顿安排一位朋友用一支小口径步枪对准他的手臂,这出行为艺术表演题名《开枪》。伯顿的作品还包括把自己关在柜子里5天,将自己钉在大众甲壳虫汽车引擎盖上等。他后来回味道:“那一刻,我即雕塑。”
作为“先锋艺术家”,约翰·多伊将伯登的艺术融入《七宗罪》片头,同时将自我夸耀和自我贬低放在一起审视——当艺术被改造成生死冒险时将产生震颤感。伯登没有采取完全殉道的方式,他自诩为世纪末的美学家,将他的优越感连同自我厌恶投射到周遭世界,并且标记了自己。约翰·多伊则走得更远,因为他身处一个病态思想及图像饱和了的市场边缘。为了产生影响,他必须放手一搏。
《七宗罪》体现并探讨了这种钝力策略。在类型电影的包装下呈现前卫艺术的思想与实践。电影的外壳是惊悚片,具体来说是 20世纪70年代西德尼·吕美特执导的那种充满都市气息的警匪片:在赴新职上班的第一天,约翰·米尔斯(布拉德·皮特饰)对妻子特蕾西(格温妮斯·帕特洛 饰)说:“谢皮科要开始工作了。”(“你可能得先解决眼角上的眼屎,谢皮科。”她睡眼惺忪地回应道。)更重要的是,《七宗罪》还算是刻画连环杀手的影史里程碑。这种类型的电影始于1931年弗里茨·朗的电影《M就是凶手》。影片中那位心怀内疚的恋童癖由彼得·洛出演。这个角色既是欲望无法满足的受害者,也是20 世纪早期现代社会残缺面的衍生物。他蓄意伤害别人来表达自己的创伤感(“谁理解成为我是什么感觉?”)。除了演员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外,这部电影另一个深刻之处是为魏玛时期,充斥钢筋、玻璃的柏林小巷、为彼得·洛扮演的那个怪人汉斯·贝克特提供了无穷无尽的藏身处,使他同时躲避着警察和同行的追捕。
彼得·洛在《M就是凶手》结尾时的苦痛,后来在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惊魂记》(1960)中的安东尼·博金斯和迈克尔·鲍威尔《偷窥狂》(1960)中的卡尔海因茨·伯姆身上被加以深化。这两部孪生杰作分别用各自的手法——叙事省略(希区柯克)和寓言体(鲍威尔)——将杀人狂、怪癖与迷影情结相提并论。《惊魂记》的断奏剪辑本能地应付了海斯法典破碎的审查与观众的心理防御机制,由此预示着20世纪70年代一系列连环杀手电影的发展——在这个时代,精神病学的普及成为一个多平台增长的产业,至少涵盖纪实犯罪小说和磨坊式电影。查尔斯·曼森与好莱坞的神秘关系,以及唐·希修尔在《肮脏的哈里》(1971)对旧金山“十二宫”杀手的描述——以弗里茨·朗的视角游荡在这座城市迷宫——是这一增长的关键标志。另外还有伪自然主义惊悚片,比如韦斯·克雷文那部“曼森式”的影片《魔屋》(1973)和托马斯·哈里斯的畅销小说《红龙》(1981)。《红龙》将匡提科协议过滤掉并转化为威廉·布莱克的典故和吉尼奥尔的映射,从而制造了比《德州电锯杀人狂》更惊悚的戏剧效果。
布莱特·伊斯顿·埃利斯1991年出版了一部备受争议的小说《美国精神病人》,对哈里斯那种哥特小说的风格滥觞进行扬弃,并将对于幻觉主义社会生态的讽刺融合进去。小说讲述了一位华尔街大亨拥有连环杀手秘密身份的故事,从而将小说的风格推向血腥的极致。同年,乔纳森·戴米执导的影片《沉默的羔羊》上映,获得了奥斯卡5项大奖。影片改编自哈里斯同名小说,由安东尼·霍普金斯饰演的汉尼拔·莱克特,在他身上,诺曼·贝茨的人格和精神分析师的职业,被以幽默而可怕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这些流行文化的话题都间接影响了《七宗罪》的创作。《七宗罪》耗资3000万美元,是其制片方“新线电影公司”(因1984年的电影《猛鬼街》而被戏称为“弗莱迪的老巢”)所下的高风险赌注,用以缓解观众对于连环杀手的审美数劳。电影于1995年秋上映,辅之以神秘而稀罕的广告宣传,全球票房达到3亿美元,成为一部离奇的、悖论式的大众电影。
《七宗罪》的张力与《美国精神病人》《沉默的羔羊》一样源自一系列早已奠定的传统,同时又与这种传统保持距离。主要通过一种“有毒”的视觉风格来实现这一点,而其风格一扫警匪片故事的俗套,凸显了警匪片的精髓。同时,连环杀手的素材,由约翰·多伊所实施的“七宗罪”连环谋杀,即使没有被影片所神化,其叙事手法也拔高了影片的格调,如果不是刻意亵渎,那么它甚至有点像一出滑稽喜剧:连环杀人构成了一场演讲,演讲的内容被刻在受害者身上,由渴望感官刺激、与其玩耍的媒介结构最终传递给公众。
《七宗罪》的高概念相当自命不凡,但它令人眼前一亮,甚至眩晕。其中一个场景最具诗意地表达了这种概念。在寂静宛若教堂般的图书馆里,黄色的台灯点亮了这一巨大的空间。这是一个凝聚时代智慧的文学之地,也是一座避难所。“这些书”萨默赛特警官在巴赫的D大调第三组曲的背景旋律中踱步,并对保安感慨道,“整个世界的知识在你指尖上……而你们却在打牌。”正如《七宗罪》试图超越其前辈的血腥,电影无处不在的知识分子思想也超越了《精神病患者》过于严肃的弗洛伊德主义和《沉默的羊》中拉康式的“等价交换”;该片虽然是纯粹的商业电影,但其肌理却是宗教仪式化的。
《七宗罪》融入了不少年代错乱的元素以及工艺美学。这部电影的其中一个启示即是它可被视为当代的“古董柜”,又或者是“珍奇屋”,一种源自中世纪的建筑空间,装满稀奇古怪的东西,如同微型博物馆。《七宗罪》的第一个“珍奇屋”出现在设计师凯尔·库珀幻觉式拼贴的构思(由哈里斯·萨维德斯拍摄 ),通过潦草文字和拼接的笔记本,传达了约翰·多伊不幸的世界观及其手艺。为这些令人不安的手工字体,还有医学教科书风格的怪诞照片,伴奏是九寸钉乐队“击打”出的工业摇滚节拍。1994年,该乐队出版了一张名为 Downward Spiral的专辑,预告了《七宗罪》的极端性(同年,珍珠酱乐队出版了热门专辑 Vitalogy。这张专辑的封面被设计成一本怪诞的伪医学教科书,上面记录了一系列人类异常现象。
在后续的镜头中,《七宗罪》的“珍奇屋”主题变得更为具体。摄影机沿着约翰·多伊的公寓货架进行追拍,照片展示了作为战利品的受害者。这一镜头不仅是对电影情节的简要回顾,还将约翰·多伊的虐待狂属性,偏执的收藏癖,还有域外艺术风格联系起来。一组堆砌的番茄酱仿佛是对安迪·沃霍尔的滑稽致意。更通俗说,严谨的概念与恐怖躯体的混合暗示着一个由艾德·盖恩和达明安·赫斯特联合举办的艺术——身体的恐怖展览。可以说,《七宗罪》的杀手运行着一套独特的戒律与艺术传统。因此,约翰·多伊“致命一击”的说法(包括承认自己需要被人聆听)——像是打电话给了《M 就是凶手》中的“M”——在他导演的眼里其实是一种诉诸凶器的低语,介于自夸和讽刺性的悲悯之间。无论你对《七宗罪》有什么说法,它都不应被视为轻描淡写的作品;无论大卫·芬奇在他的第二部剧情片挖掘了什么样的矛盾冲突,他都值得我们的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