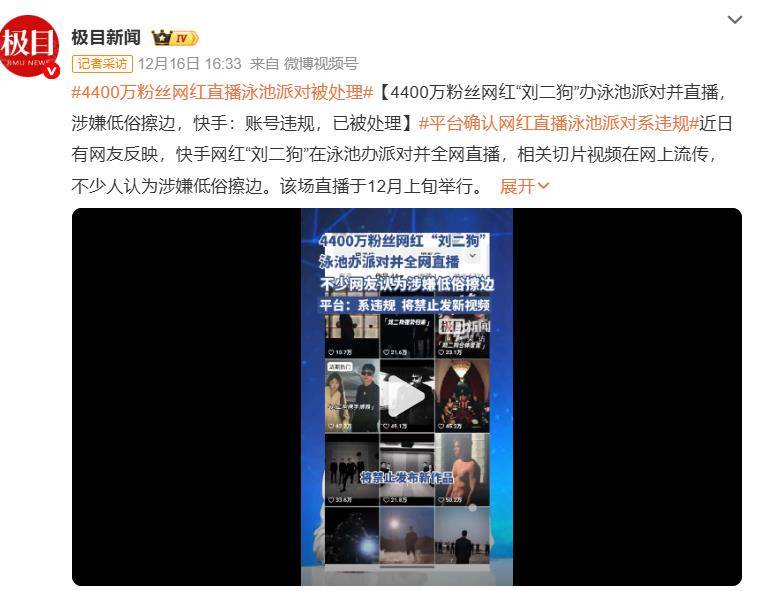这是发生在抗战时期的一个故事。
一天,一位名叫连柏生的新四军战士执行任务时遭遇日军,急忙进村躲避。正在给孩子喂奶的一位大嫂认识连柏生,急中生智地把孩子塞给了他,让他抱着孩子睡在床上。冲进房内的日伪军指着连柏生问:“他是什么人?”“我男人!”怎料,大嫂话音刚落,丈夫从地里回家了。见状生疑的敌人逼问:“他又是什么人?”大嫂咬咬牙,说:“我不认识他。”大嫂的丈夫被日军带走,再也没有回来……
后来,有记者问陈毅:“江南水乡没有山,新四军靠什么对付敌人?”陈毅回答:“靠‘人山’,人民群众就是我们最大的靠山!”
人山——正是有了人民群众这座靠山,在山区,八路军、新四军如鸟投林;在平原,在水乡,八路军、新四军如鱼得水。中国共产党开辟的一块块敌后根据地,成为埋葬侵略者的汪洋大海。
【一】
1937年11月8日,刺骨的寒流由北向南。朔风之中,太原、上海相继陷落。
延安,密切关注着战局走向的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就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发展敌后游击战争。他将建立抗日根据地比作“下围棋”: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之据点和我之游击根据地则好似做眼。
一天前——1937年11月7日,共产党开辟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诞生。紧接着,一一五师以吕梁山为依托,一二〇师以管涔山脉为依托,一二九师以太行山脉为依托,相继创建晋西南、晋西北和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毛泽东指出:“华北正规战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八路军将成为游击战争的主体。”他由此作出了被历史证明最为英明的决定:到敌人后方去!
“东进”,“太行”,两个在战火中诞生的孩子的名字,记录了八路军挺进抗日敌后的历史性瞬间。
1939年2月12日,一个小生命降生了。
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之子罗东进回忆:“母亲抱着我找父亲起名字,父亲正在部署一一五师主力东进事宜,随口说,叫东进吧。”
襁褓中的罗东进被母亲林月琴一路抱着奔赴山东,成了这支八路军队伍中年龄最小的一员。
一个月后,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与妻子汪荣华的第一个孩子在太行山呱呱坠地。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刘伯承听说是个男孩,哈哈一笑,就叫太行吧!
回荡在沂蒙山七十二崮的战歌,与嘹亮在巍巍太行的军号遥相呼应。一东一西,两处方圆八百里的山地,成了华北大地的铁壁铜墙。
茅山,如同一枚碧玉纽扣,系于沪宁两大城市带腰际。
茅山之巅,36米高的苏南抗战胜利纪念碑巍然耸立。远远望去,仿佛刺向苍穹的利剑。
纪念碑前放鞭炮,纪念碑下听军号——“丰碑奇号”,已经成为今日茅山景区一大奇观。尽管地质专家认为,这一现象是建筑结构与山体形成的特殊声场所致,当地的人们却更愿意相信这是当年新四军冲锋的号声在回响。
新四军挺进江南的第一声军号,吹响在1938年6月17日雨雾茫茫的早晨,粟裕率抗日先遣支队连续突破日军三道封锁线,在镇江城外打了一个胜仗——韦岗之战。
陈毅赋诗祝贺:“故国旌旗到江南,终夜惊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让敌人心惊的是,6个月时间,挺进江南的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就建立起面积1.5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00万的茅山抗日根据地,成为全国六大山地抗日根据地之一。
时任新四军先遣支队参谋张铚秀回忆:“刚到江南的时候,不少老百姓见新四军连机枪都没有,不免有些误解,认为这样的队伍还能打鬼子?事实很快让人们信服了。”
7月1日,党的生日,新四军捣毁宁沪线上的新丰车站;8月12日,新四军攻占挺进江南的第一个县城句容县城;除夕之夜,新四军风雪出征,全歼日军青木大队……江南大地,开始流传起这样的歌谣:“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
茅山,毛泽东亲自为新四军选定的桥头堡。还在1938年5月4日,他就在给新四军的电报中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能够克服这些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正是这一史称“五四指示”的电文,为新四军开辟敌后根据地指明了方向。
陈毅曾经用“惊喜交加”形容初到茅山时的心情——“喜的是部队终于安全挺进到达指定地点;惊的是茅山在游击战的地形意义上完全不合乎我们的要求”。不同于三年游击战时期山高林密的闽赣山区,当时的茅山实际上是一片植被低矮稀疏的“童山”。
日伪军重兵布防,新四军隐蔽困难。面对重重挑战,陈毅鲜明提出“人山”思想:“江南地区虽然是水网地带,没有深山密林,但这里有广大的抗日人民,也就会出现许许多多人造的深山密林。我们战斗在由人民群众组成的深山密林之中,就能生存和发展,就能打胜仗。”
1939年冬,江南抗日义勇军奉命从常熟地区西撤,36名伤病员留在阳澄湖畔的沙家浜芦苇荡中养伤。
败血症和洪水,先后夺去11个年轻的生命。25位幸存者就像25粒芦荡火种,不但保留下来,而且播撒开去,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在当地民众中发展出一支4000多人的抗日武装,像一把钢刀,直插敌人心腹之地。
【二】
奔腾的沁河,穿越太行山与中条山之间的峡谷,成为两大山脉的自然分界线。
沁源,太行山脉深处的一座小县城。1942年10月,华北日军推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矛头直指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占领沁源的日军,妄图把这里打造成“山岳剿共实验区”。
共产党一声令下,沁源人民坚壁清野。
忍痛砸掉带不走的坛坛罐罐,扶老携幼撤入苦寒的深山。没有一个群众向严寒低头,更没有一个向日寇投降。
整整883天,沁源军民经历2730余次大小战斗,毙伤日伪军4000余人。尝尽“剿共”苦头的日军在付出惨重代价后不得不逃离沁源,所谓的“剿共实验”被迫黯然收场。
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赞叹: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城!
《解放日报》在题为《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中指出:经过多次的反“扫荡”战斗与围困敌人的战斗,八万人口的沁源,成了敌寇坚甲利兵所攻不下的堡垒,成了太岳的金城汤池,人民以切身的经验,确信共产党领导的正确。
“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一件八路军缴获的日军大衣,有着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
1938年冬,八路军总部转移至太行山西麓的山西潞城县北村。一个风雪之夜,民兵杜春兰替总部送急信,朱德见小伙子衣着单薄,顺手脱下这件大衣披在了他身上。
带着总司令体温的大衣,温暖了太行的严冬。在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的笔下,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她在秋收的行列里,发现一个身背一百五六十斤糜子的老八路,走近一看,竟然是朱德。史沫特莱写道:“朱德穿着自己打的草鞋,奔波在烽火连天的抗日前线;他通宵达旦地工作,竟和战士一样每月只有一块钱的津贴,因而不得不戒掉了纸烟。朱德用最大众化的语言诠释了这一切:‘八路军是穷苦人民的军队,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当兵的,都是为人民谋利益的。’”
“1942年,那个数九寒冬天,日本鬼子呀,集中好几万,包围了马石山……”一段胶东大鼓,道出了惨烈的一幕——1942年11月23日,1.3万日伪军将方圆40公里的马石山地区围成铁桶,妄图绞杀包围圈内的2万多抗日军民。26艘舰艇封锁海面,10架战机低空盘旋。
生死之夜,八路军冒着弹雨“三进三出”包围圈,以牺牲400多人的代价,营救出6000多群众。平均每救出15个群众,就有一位官兵献出生命。
22岁的八路军战士峻青也在突围的队伍中。突出重围的当天晚上,他含泪写下生平第一篇小说《马石山上》。
峻青生前回忆:“八路军原本可以转移,但是,在这个时候,不可能放下群众不管,所以就不停地冲锋,救出一批群众再返回,失去了夜色掩护,还在往包围圈内冲,直到战斗到最后一刻……”
这一战,涌现出两位同名同姓的英雄。胶东军区13团7连二排六班班长王殿元带领全班9名战士,为掩护群众转移,全部壮烈牺牲;胶东行署公安局警卫连指导员王殿元率官兵冲破敌人层层包围,掩护群众脱险。17位战友战死,王殿元身负重伤,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日军同归于尽……
“马石山十勇士”“马石山十八勇士”,这些永不磨灭的英雄番号,承载着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生死与共的不变情感,如同昆嵛山72峰,永远挽着黄海的浪涛。
1944年夏天,延安迎来了美军陆军上校戴维·包瑞德率领的观察组。此行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回答美国政界的一个疑问:在国民党政府完全断绝军饷的情况下,八路军为什么能够坚持敌后抗战?
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等向美军观察组详细介绍华北八路军的抗战情况,一问一答,整整三天。
彭德怀说,共产党实行民主,坚决依靠人民,一切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发动与武装人民参战,使战争真正成为全民战争,这使我们的抗日力量增强到千百倍。
“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几乎在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的同时,中外记者团也来到了陕北。传唱在延河两岸的这首民谣,引起了英国记者冈瑟·斯坦因的好奇心。
在延安城外的山沟沟,斯坦因认识了劳动模范杨步浩。得知这位大字不识的农民也能参加选举,斯坦因开始时半信半疑。几天之后,当他目睹当地的一场选举,这位英国记者信服了。
斯坦因把“豆选”写进自己的著作《红色中国的挑战》:“在中国这块最落后的区域,许多农民过着一种新的、有希望的生活。他们已从古老的封建主义中被唤醒了。”
不仅仅是在陕北,在华北、在苏中,在一处处敌后根据地,被共产党唤醒的千百万民众,开始用这种原始的方式,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凝聚起同仇敌忾、一致抗日的磅礴力量。
【三】
上世纪六十年代,电影《地雷战》《地道战》先后上映,两部影片均取材于真实的战斗生活。
《地雷战》中的民兵队长“赵虎”,为“爆破大王”赵守福与于化虎事迹的合二为一;女民兵“玉兰”的原型,则是巾帼英雄孙玉敏。
赵守福原名赵良桂,于化虎原名于晋生。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蒲扇般的大手拍在赵良桂肩头:“海阳是片福地,希望你守住这片福地,我看就叫赵守福吧。”他又对于晋生笑道,“晋生化虎,你叫于化虎怎样?咱中国人是龙是虎,龙腾虎跃,暴风骤雨,这就是小鬼子的大灾大难!”
海阳处于丘陵地带,地势复杂,尤其赵疃村、文山后村、小滩村,山石林立,山道如蛇,易于设伏,正是地雷战的天然猎场。
1942年惊蛰时节,山上的苦苦菜刚刚发芽,赵疃村惨遭日军血洗,将近300具遗体怒目苍天……
几天之后,23岁的赵疃村民兵队长赵守福和28岁的文山后村民兵队长于化虎召集会议。摇曳的麻油灯下,几十个民兵对着一筐黑火药起誓:“以血还血,以雷还雷!”
复仇的怒火迸发出岩层深处的震颤——砸碎的犁铧熔铸成一枚枚“铁梨花”,乡村石匠的开山锤成了砸向日寇天灵盖的战斧。抗战时期,海阳敌后武装力量毙伤俘敌1025 名;涌现出赵疃、文山后、小滩三个“特级模范爆炸村”和赵守福、于化虎、孙玉敏三位全国民兵英雄以及600多名县级以上民兵英雄。
从山东到河北,无处不在的地雷阵,成了侵华日军步步惊心的“噩梦”。日军独立第三旅团第六大队代理大队长菊池重雄在日记里写道:“地雷战使我将官精神上受威胁,使士兵成为残废。尤其是要搬运伤员,如果有5人受伤,那么就有60个士兵失去战斗力。”
海边的夕阳,将赵疃村的青石墙染成黄昏血色。80年过去,当年埋雷的羊肠小道已经变成观光步道,但岩缝间偶尔露出的陶片与铁屑,仍在讲述着那段石破天惊的岁月。地雷战纪念馆内,一位抗战老兵的留言诠释了一个真理:“地雷会锈蚀,但一个民族在绝境中迸发的创造力,永远不会生锈。”
保定市冉庄村,电影《地道战》的拍摄地,至今仍保留着3公里的抗战时期地道。当年,冉庄人民依托16公里的地道网,配合八路军对敌作战157次,毙伤日伪军2100余人。
“地道战,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百万……”冉庄地道战纪念馆提供的数字表明:到1944年冬,冀中抗日军民开挖出总长度超过1.25万公里的地道网,遍布8000多个村庄。英国媒体报道称:“河北农民用铁锹和箩筐建造的地下迷宫,足以令罗马工程师惊叹。”
艾斯·杜伦,美军观察组成员。1944年11月,杜伦专程来到任丘县皮里村考察地道。
就在杜伦惊叹于自己的见闻时,日军悄然来袭,杜伦被紧急转移到村民娄庞氏家的地道。
日军发现了地道口,朝着地道中放水灌烟。
地面上,不时传来日军的吆喝声、打骂声和阵阵枪声,地道内却几近寂静无声。
傍晚时分,日军悻悻离开。杜伦钻出地道才得知,日军逼迫娄大娘供出他的去向,大娘宁死不屈,被日军砍断了4根手指;民兵娄福荣也因拒绝“合作”,被敌人用烧红的铁锨活活烙死。而在同一条地道内,冀中军区第九分区司令员魏洪亮的妻子萧哲担心孩子发出动静,竟然把怀中的孩子捂得停止了呼吸。
杜伦被深深震撼了:“有这样好的人民,中国必胜,日本必败!”
在高高的山冈上,在密密的丛林中,在遍野的青纱帐和芦苇荡里,抗日军民创造出一整套令日寇闻风丧胆的战法: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破袭战……这一幕幕战场奇观,构成了人民战争的威武活剧。
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这,就是中华民族赢得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的深层密码。(贾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