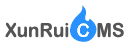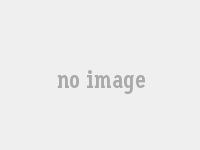看了《浪浪山小妖怪》,这部电影的英文标题是“nobody”,讲了一群无名之辈冒充唐僧师徒取经的故事。

四人主角团是典型的“言说共同体”,他们通过共享语言实践、目标追求和互动机制构建了共同身份——我们是取经人。“假冒唐僧师徒去取经”这一荒诞目的,是他们语言实践的中心,被他们不断地分析、争论。观众们可以通过人物的互动以及谈话的内容,联想到现实中、尤其是职场中的各种实际问题,这是本片的一大魅力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见解。

我想着重谈一下最喜欢的角色,也是这个团队中的异类:猩猩怪。
猩猩怪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口吃。这种口吃偶尔会被另外两个状态所占据,即“沉默”和“流利”。
在山洞中找到猩猩怪的时候,它是沉默的。家人被大王洞杀害的创伤,让它一直不愿离开这里。 山洞是它的心理防御机制的具象化,通过物理上的与世隔绝,来摆脱暴力的威胁。
但是另外三位角色的入侵,打破了这一局面。青蛙视若珍宝,能为他占据象征界一席之地的号码牌,对猩猩来说是符号暴力的冰山一角。这使它无论如何也无法认可其他三人讲述的取经故事,不愿意被纳入象征界,不想被符号秩序规训和异化的它,干脆用沉默拒绝了语言这把通往象征界的钥匙。
通过语言进入社会关系网络这一过程,本身也充满暴力性,所以被强行带出山洞之后,猩猩怪只能用不断哭泣来表达反抗。在未融入这个言说共同体之前,语言是另外三位角色的特权。当然,离开山洞直面创伤的恐惧情绪,也在漫长的哭泣中被释放,这是最终能开口说话的契机。

在故事中期,小猪妖和蛤蟆精企图用话语对猩猩怪塑形,企图将自己的欲望灌注于猩猩怪。于是一遍一遍地重复着仪式性的话语“你是齐天大圣”。
“凡是对言说体制的触犯,都将遭到严厉惩罚。主人公的口吃正源于他无法确定,自己想要言说的东西能否得到言说体制的放行。伴随着内心的迟疑而显现出来的,是话语的断续与时间的延宕。”(1)
才刚刚试探性的进入关系网络的猩猩,本能地恐惧着自己在说出这种冒犯性话语后会遭到“惩罚”。更进一步地讲,说出这句台词,无疑是要求猩猩否认自我,去接受英雄符号。在“自我”和“齐天大圣”的认知之间,有一道巨大的鸿沟。
旅途中的经历,在改变着猩猩,也在慢慢填补它自我认知的鸿沟。获得装备、纠正站姿、击败老鼠、被送锦旗的经历,它代表着符号秩序对他这个“伪装者”一次一次的放行。以至于它终于可以不再惧怕“言说体制的惩罚”,放弃了“齐大天胜”、“齐天大大胜”这样的缓冲垫。

故事后期,猩猩怪在悬崖边“流畅”地喊出了“我是齐天大圣”。这并不是询唤仪式中对他人指令的被动应答,而是对符号秩序带有反叛性的自我命名。
但此时此刻,与先前一帆风顺、频频遭到放行的场景不同。符号秩序已经开始阻却、开始惩罚这种对言说规则的触犯行为。枷锁、嘲笑、否定,是这种阻却和惩罚最直观的表现。正如最后四位主角使出组合技,修为消耗殆尽后被打回原形一样。棍子打断、衣服和饰品被夺走,
此时此刻猩猩的每一声呐喊都是对之前积累的不可逆转的消耗。这种消耗性、牺牲性的反叛,成为了这段剧情感染力的核心,同样也会被观众所铭记。
正文就是以上这些,黄大仙我也写了点,关键词是“行为搬演”似乎也不太需要展开。这篇的整体思路来自《“口吃” 是一只小鸟——三岛由纪夫 《金阁寺》的微精神分析》,中间标(1)的部分是引用的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