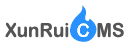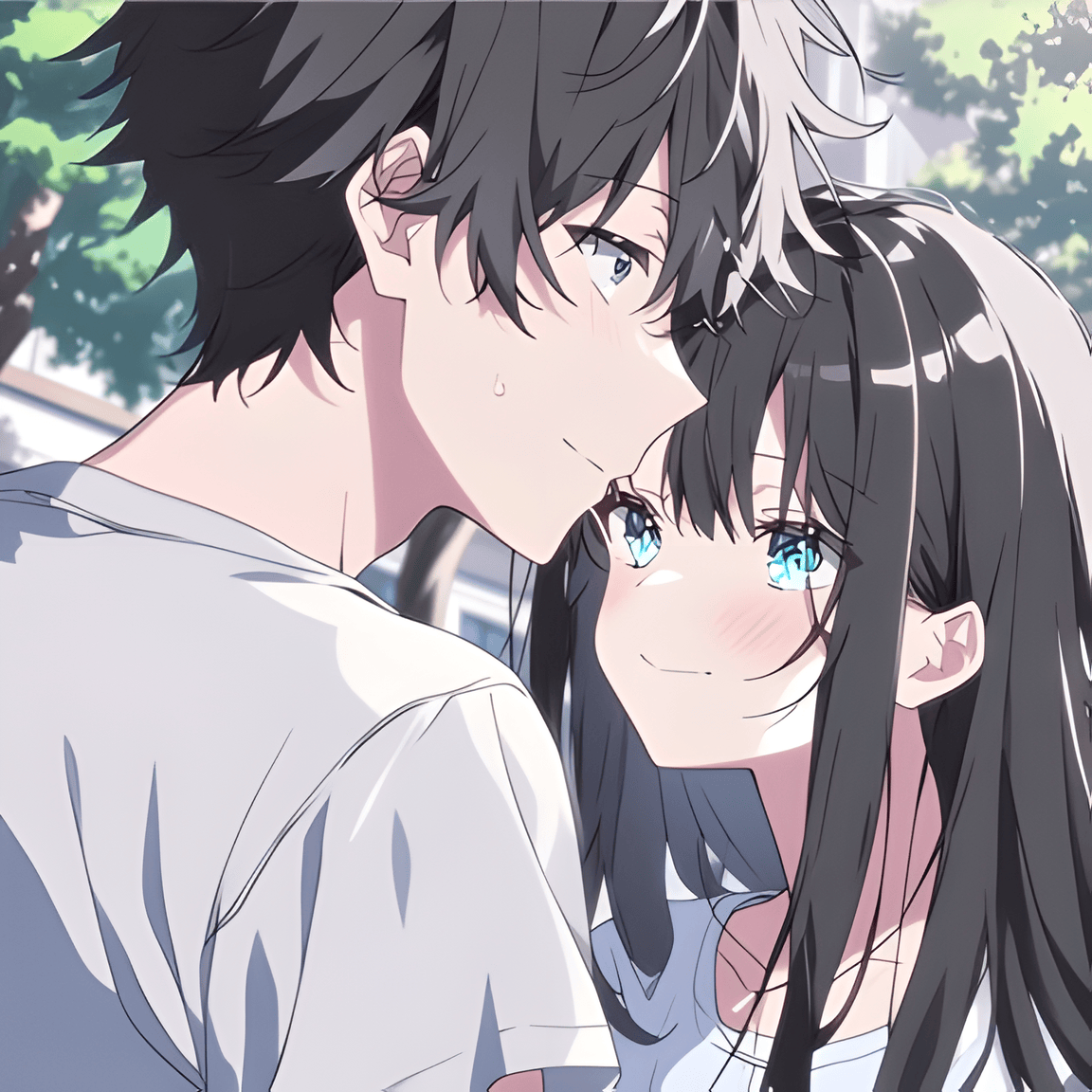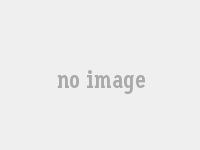文|云初
编辑|云初
本文陈述所有内容皆有可靠信息来源,赘述在文章结尾
《——【·前言·】——》
程述尧娶过三位大美人:黄宗英、上官云珠、吴嫣。他享尽名利,却收获爱情灾难。这三个女人背后的故事,折射着一个男人一生的凄凉结局。

初婚黄宗英——甜姐儿的天赋与婚姻坎坷
1945年秋,北京燕京大学毕业的程述尧迎来人生重大转折。他从北平北上,与一位曾演话剧的黄宗英结婚。这位30岁的戏坛女演员,曾在曹禺剧中担纲女主,外形清新可人,被称为“甜姐儿”。结婚当天,程述尧并未感受到答案里透露的锋芒,只是觉得眼前这位妻子落落大方,值得依靠。
婚后短暂蜜月期,两人回到大北平,程述尧在南北剧社任社长,黄宗英出演剧目不多,却精力满满。剧社没有盈利,多靠他个人掏腰包撑着,生活虽不富裕,但温情依旧。他对妻子支持职业,四处奔走为她争取角色,出钱租场子,又劝人造势,却没想到这一切很快被现实打脸:抗战胜利后票房冷淡,剧社亏损严重,黄宗英赴上海拍戏,却在那里留恋上了搭档赵丹。

程述尧被无情抛弃。1950年前后,黄宗英与赵丹同居,家庭破裂女方提出离婚。他反复挽留,苦劝无效,却依然无怨无悔。曾为前妻及其亲人出钱救急,即便被“绿”,也继续关心她家境。那份宽容,在朋友看来是“好男人”,但换来的是无情判决:第一次婚姻结束,他光环瞬间破碎。

次娶上官云珠——红颜名伶的争议与离散
上官云珠,本名韦亚君,江苏江阴人。第一任丈夫为镇上富商,三年后嫁入南京名门。之后进入演艺界,又先后嫁与剧作家姚克和京剧演员蓝马。凭借电影《丽人行》《乌鸦与麻雀》等片出名,她被誉为“上海第一代电影明星”。1951年,云珠迎来新生,与程述尧结婚。
对程述尧而言,上官云珠带来短暂的荣耀。他用剧场资源、传媒资源,将前妻失败的教训意外转化为对这段婚姻的施力点。他相信娶名伶能让自己走回人生巅峰。两人育有儿子程韦然,名伶与才子联手似有良性开端。

却没想到三反五反运动席卷全国。他身为剧场经理,被指贪污,被降职,从公众的关注中心掉下。他没有金钱,却仍信妻子那份荣耀。上官云珠看重的是事业与未来,认为程的落魄已经拖累自己。她离婚时未参与争子抚养,却带着儿子离去。程述尧再一次追不上婚姻了。第二段婚姻以破灭作结,他再吃一回情怀的苦果。

伉俪情深,换不来命运宽容
1970年代末,程述尧已年近花甲。他的两段婚姻成了旧影,只留下儿子程韦然在远地读书,一年难见一面。彼时,他已无剧社、无官职,靠稿费维生。朋友介绍他认识吴嫣——一位曾在部队文工团任职的独身女性。
她不再年轻,却有温和耐性,熟悉生活节奏。与程述尧初识时,吴嫣刚从文工团内调,工作寂寂无闻,日子平稳且寡淡。两人几次通信相互试探,一无权势,二无利益,渐渐确认彼此都无再博名利的野心。程述尧主动提出同居,吴嫣答应后,两人便在一间老公寓里一起生活。

这是他第三段婚姻,没有大婚仪式,也没有旁人祝贺。搬家那日,程述尧只带了三箱旧书、一张老照片。书架上,他自己编写的剧本沾满灰尘。他不再写大剧,只在杂志上偶尔发些回忆文章,一年能收到一封编辑的感谢信已算惊喜。
吴嫣很会过日子。冬天用旧床单做棉拖鞋,夏天将菜根泡醋调味。他们住的小屋厨房小如猫洞,她总能做出三四样小菜。他常边吃边说“比我当年请人下馆子都强”,话不多,但温度够。
这一段婚姻是他晚年唯一的温暖。无争执、无期待、无激情,有的只是一天又一天安静共处。程述尧常坐阳台晒太阳,脚边放一壶茶,远处没风景,墙皮斑驳,光透过格栅映在他的白发上。他时常盯着楼下发呆,像在等什么,又像谁也不等。
有时邻居来串门,说“你老婆真是个好人”,他只是笑笑,不言语。他从未说爱,也不再承诺。他太清楚,这不是年轻人求新鲜的结合,而是两片旧木板拼成的温热炉火。

尘归尘,人归寂
进入90年代,程述尧几乎不再被外界提及。他的名字只存在于过往剧目列表中,一年中也难有邀稿。他身体变差,常在清晨醒来时咳嗽不止,吴嫣端水喂药,从不多言。
晚年最打击他的是儿子程韦然公开反对他写回忆文。他们在信中发生分歧,儿子在信里直言:“你写的,不是真实的历史。”这让他好几天饭都咽不下。他开始怀疑自己存在的意义,甚至把早年收集的剧本草稿撕了好几页。

吴嫣劝不动他,只能坐在客厅静陪。她翻书、缝衣、收拾碗筷,他一个人坐在角落,不言语。那一年冬天特别冷,外面下雪,他看着窗外雪落在屋瓦上,似是看到自己过去几十年:辉煌、热烈、迅速化雪。
1996年某天傍晚,他坐在书桌前,手握钢笔试图写点什么。落笔未久,他头一低,伏在稿纸上安静不动。吴嫣发现后拨打电话,医护赶到已无回天之力。他离世时桌上放着两样东西:一张发黄剧照与那封没回的信。
丧礼极简,几位旧友来吊唁,无媒体报道,也无旧剧社表态。人走后,小屋归于寂静。吴嫣按遗愿不设灵堂,将遗物分发给老友,仅留那张剧照与一册旧笔记。她一生未再婚,几年后也在同处离世。
程述尧一生,娶过三位大美人,爱过、伤过、孤独过。结局是坐在旧沙发里,留下一屋旧书和几页手稿。他没留下名剧,也没留下戏梦人生,只留下一句“人这一辈子,太难了”。